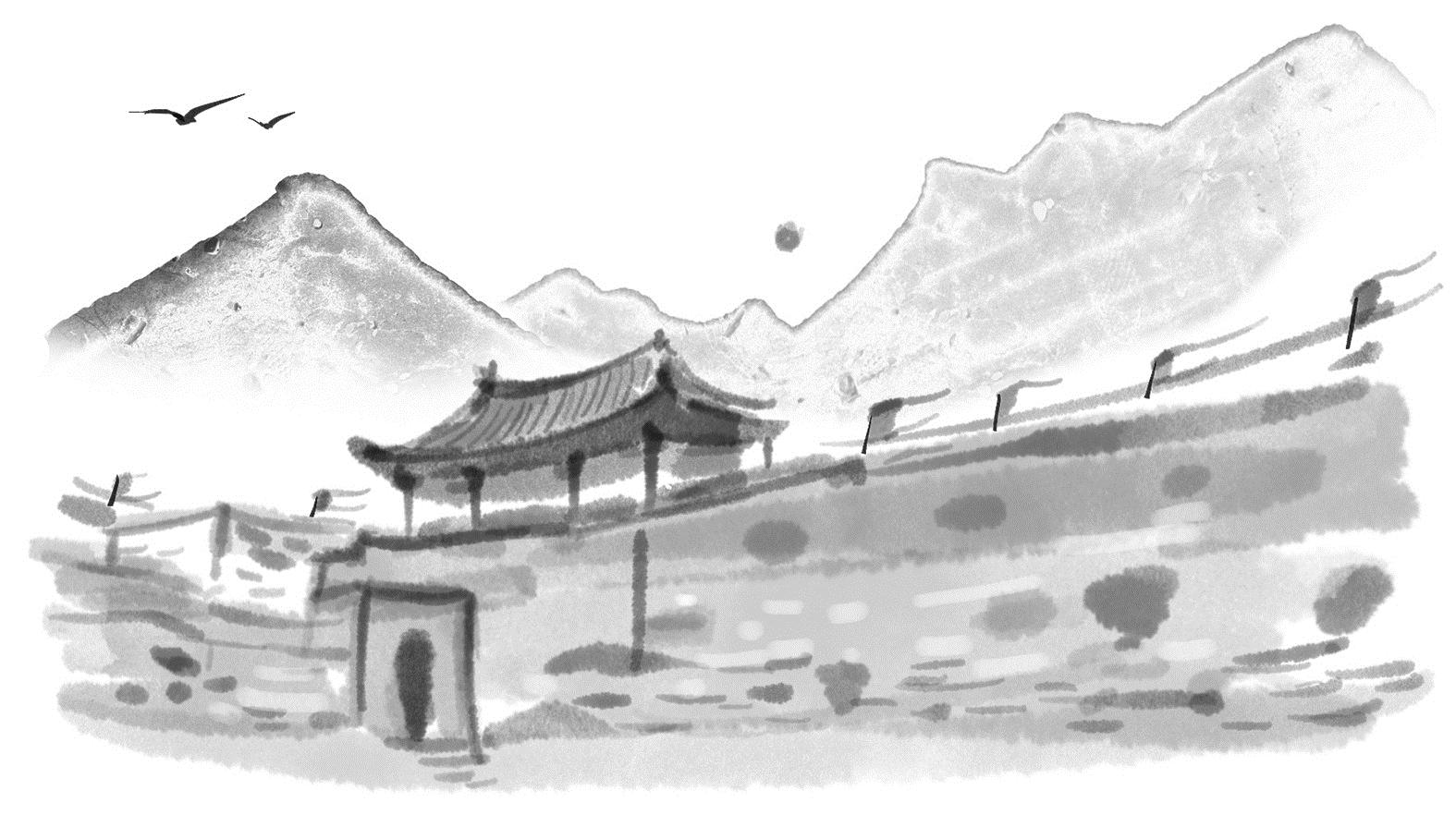文<袁甲清
到了银川,朋友说镇北堡是要去的。
车子出城后,驶入郊外空旷的柏油公路,天空瓦蓝瓦蓝的,映着洁净明亮的路面,两旁栽植了西北常见的杨树和柳树,枝干和叶子簇簇向上,在艳阳里摇曳。
让人怦然心跳的是,贺兰山竟离我那么近,公路几乎是贴着山影延伸。贺兰山是青灰色的,岩质山体沟壑纵横,皱褶起伏,苍莽如万马奔腾。
受边塞诗及历史故事的影响,我印象里的贺兰山是刀光剑影、战马嘶鸣,是黄沙征战几人回。贺兰山居于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的接壤地带,也是沙漠和黄土高原的地理分界。旧时一旦气候变化,生存环境恶劣,获取食物困难,游牧民族常伺机南侵,引起农耕民族的反弹对抗,这种反反复复的拉锯,在历史上曾经多次上演。事实上,这也是沿长城线的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融合地带的常态。
地理上,贺兰山阻断了北地寒流和沙漠的侵蚀,成就了黄河两岸银川平原的富饶和美丽。
公路两边的田畴里,正是瓜果飘香的繁盛景象。很多瓜果叫不出名,但葡萄和枸杞是认识的,它们的园场一片接一片从车窗忽闪而过,饱满的紫葡萄、殷红的枸杞,十分耀眼。远处山脚下,似有曲水蜿蜒、只鸟低回,该是一块小湿地吧。
这时候,我的脑海里,突然蹦出唐朝诗人韦蟾的诗句:“贺兰山下果园成,塞北江南旧有名。”从唐朝,或者更早时候,这塞上勤劳的人民,已亲手铸就瓜果之乡的美名,编织了江南一般的田园风光。如今,这番贺兰山下好风光,又让我们领略到了与大西北迥异的塞上江南风貌。
40分钟后,车子到了镇北堡古城,也就是眼前的西部影城。
这里呈现着与来时路上完全不一样的风景。目光所及,皆是黄色。黄色的墙垣、黄色的房子、黄色的基底,整个古城都是黄色的,原始的黄、粗粝的黄、古朴的黄。这种黄色甚至溢出城墙,向着天空和四周蔓延扩散,扩散成无边的荒凉。
颓废的墙垣和错落有致的房子都是泥土做的,这里的泥土富含盐碱,风干日晒后坚硬如石,又泛着盐碱的白花。城墙古老、颓废、沉默,仿佛把你带向数百年前的时间深处。
防御北方游牧势力,明朝的做法是“高筑墙”,不断增补或者延建原来的长城,并在绵亘万里的长城沿线设置边防重镇、关隘堡垒,构筑严密的军事防御体系,其中,宁夏即隶属于九边九镇防御体系中的一环。
为防御贺兰山西麓和河套地区游牧部落的侵犯,明弘治年间,在贺兰山东麓置镇北堡,修城筑堡,派驻戍卒,遂有了镇北堡要塞的雏形。像这样的堡寨,宁夏境内有60多座,它们作为明代防线的重要据点,像锁链一样拱卫边境安宁。
据史料记载,镇北堡城垣周长一里一百六十步,距贺兰山30里,距宁夏城40里,驻守军160名,军马83匹,防区下辖瞭望墩台7座,墩与墩之间相隔数里,每个墩台配有军士3人,负责观察敌情。每遇敌人来袭,白天升烟,晚上点火,向堡内驻军传递信号。
清乾隆五年(1740年),宁夏发生大地震,镇北堡兵营遭震毁。两年后,清政府在“老堡”200米处重建兵营,形成一座比“老堡”略大的土城堡,是为“新堡”。这种古堡,当地人称为“土围子”,城堡墙体没有一块砖石,完全用黄土夯筑而成,是中国西北地区特有的覆土建筑。
漫长的防御体系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,但明代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财政和人力成本,不堪重负,再加上朝廷腐败以及后续皇帝的昏聩怠政,这条军事防线逐渐衰弱没落。到了清代,一边固守边防,一边开始采取“攻心”战略,不断分化瓦解草原各部落势力,随着察哈尔部被清廷征服,辽阔的草原成了清政府的一片坦途,绵延长城的整条防线彻底失去了当初的功能,城池、堡寨等防御设施逐渐废弃,镇北堡也被时代遗弃,从此湮灭于茫茫历史烟云。
风刀霜剑的侵逼,再加上人为破坏,这片土围子逐渐坍塌,成了断垣残壁,就像边塞上曾经出现过的那些显赫一时的城池那样,逃脱不了被风尘淹没的命运。没人去在意它了,因为在西北深处,那太过平常,甚至平常到有点令人生厌。它一度沦为牧民的羊圈。
直至上世纪八九十年代,一个名叫张贤亮的作家发现了镇北堡,将其从历史的重重尘烟中拎出来,包装、打扮、还原,重新赋予它历史的、地理的、文化的含义,遂成就了镇北堡西部影城今天的辉煌。
走过城堡,那些星星点点的土房子,因为以电影或电影里的经典人物或场景命名,成了一处处景点,譬如九儿居、铁匠营、酒作坊、柴草店、招亲台、盘丝洞、月亮门、龙门客栈等。游人们热热闹闹的,他们身临其境地体验到电影里或者现实中的西部风情和西北民俗。
历史照进现实。塞上江南的胜景、铁血贺兰山历史风铃的回响,在此完成了奇妙的统一。我想,这正是镇北堡的独特魅力所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