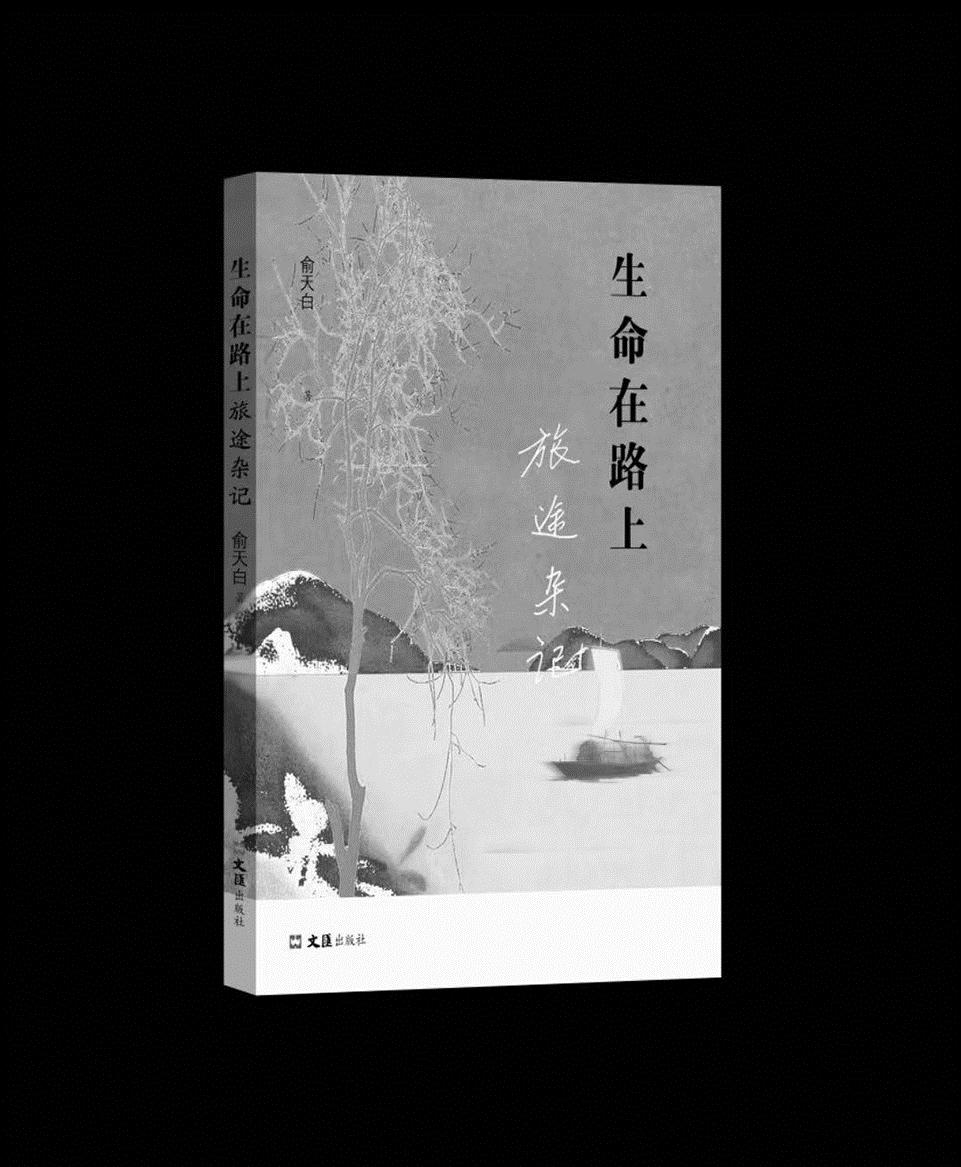近日,知名作家俞天白的长篇纪实作品《生命在路上:旅途杂记》出版。该书收录了作者1982年至2009年期间的旅途杂记,以日记体形式,记录了参加作家笔会、编辑组稿、记者采访、文化与经济研讨等文化活动时的所为、所见、所闻、所思、所游、所交往,按出行时间顺序排列。无论是黑龙江的顺流漂行、长江大小三峡的溯行、沿长城的河西走廊寻踪行,还是从珠江三角洲到海南岛腹地的穿梭行、西南边陲的环行、新疆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边沿行,旅途劳顿而笔耕不辍。作者坚信,“生命就是在路上”。他在该书题记中写道:“生命就是一种经历,人生如逆旅,都意味着在路上。这是踏踏实实的腿脚行走之路,也是琐琐碎碎的日常生活之路,更是坎坎坷坷的与命运抗争之路,就看你准备获取什么。”“回望我这一条生命之路,时代、社会提供给我足够的条件,让我游历了不少地方,直至看山仍是山,看水仍是水,最大的价值,也就是沿途的风景。”该书文笔生动,写景记事详细,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和史料价值。本报特摘选书中部分内容,请读者跟随作者一起徜徉生命之路,领略“沿途的风景”,感受“岁月的温度”。
□ 俞天白
生命就是一种经历,人生如逆旅,都意味着在路上。这是踏踏实实的腿脚行走之路,也是琐琐碎碎的日常生活之路,更是坎坎坷坷的与命运抗争之路,就看你准备获取什么。当我陷于生活烦恼或者工作困顿的时刻,总是拿旅途艰辛一词勉励抚慰自己,以至形成了这样理念:生命就是在路上。如今垂垂老矣,拥有足够的资格,确定这是对生命最恰当的概括。
我很少有真正概念上的旅行,无非都是因公因事的所谓“出门”或“出差”,零零碎碎的,其路线,仅国内统计,相对完整的有六条,差不多涵盖了除西藏和台湾以外的整个中国:黑龙江的顺流漂行;长江大小三峡的溯行;沿长城的河西走廊寻踪行;从珠江三角洲到海南岛腹地的穿梭行;西南边陲的环行;新疆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边沿行……
最典型的,是河西走廊之行。都说,不到大西北不知中国的宽广,不到河西走廊不知中国的多元。我先到大西北,到过西端的伊犁,南端的喀什,而后走通了河西走廊,可以说我用双腿丈量了祖国的广度与深度。巧的是,1997年8月4日,我从长城东端“老龙头”开始,断断续续地经明长城、秦长城到达长城西端堪称“老龙”之“尾”的嘉峪关,再到敦煌,验证了河西走廊是如何实现多元的,正是8月月尾。正当我来到这个世界整整一个甲子,在一个不经意间,以如此完美的方式,理解了作为华夏之子所存在的环境,以及如何才能体现生命的价值。这不是上苍刻意帮我确定“生命在路上”的原理,还能做什么解释?
日本动漫大师宫崎骏在《千与千寻》中说:“我不知将去何方,但我已经在路上。”这是指那种不确定结果的努力,在路上才有希望,才能理解生命价值何在,却是确定无疑的。今天,我借助整理旅途上的所见所闻,审察现实,追溯历史,再次肯定,生而为人,生命总是意味着凭借对客观世界的认知、互动、融洽而展示存在,其中,难免要不断肯定、否定;否定、肯定。最雄辩的验证就是在路上。正如黑格尔在《美学》中所说,“凡是始终都是肯定的东西,就会始终都没有生命。生命是向否定以及否定的痛苦前进的,只有通过消除对立和矛盾,生命才变成对它本身是肯定的”。肯定与否定的转换及其包容艺术,包括文学创作的艺术活动尤其如此。如果只求温饱,满足肉欲,古人早已定义:行尸走肉。这与“人”字无缘。只要持这一生活取向,都是展示生命“在路上”的“一种经历”;意识到这一点,不论人生还是文化艺术,生命之树才能常青。
关于所记时间,从1982年到2009年。之所以截取这一时间段,一是我自幼养成的写日记习惯因故中止,到20世纪70年代末才恢复,但也只是用最简单的句子,记录生活要事以备忘,到江西,住在南昌梅岭“共大”总校三个月,协助出版社采写该校校史,为此,到过革命根据地井冈山茅坪、茨坪、黄洋界以及庐山等,赣水之滨留下了我不少足迹,而后以文学杂志的编辑和作家身份,到长沙、广州等地都是如此,直到1982年,才开始有了以《旅途杂记》为名的记录。其间,我到过欧洲,从地中海到波罗的海……但都没有在此书中留迹,因为我首次出国,是以中国作家代表团成员的身份,到意大利参加蒙德罗国际文学奖活动,而后,又应日本经济新闻社的邀请,访问日本。当时出国是一件很新鲜的事,都及时写了观感发表于报刊,与读者共享,然后收录于我的散文随笔集中。包括我到德国探亲时在欧洲的游历。至于到俄罗斯、美国旅行,虽然有记录,但都是旅行社组团,所见所闻都是批量的、出自规定的版本,不值得增加此书的篇幅。收录于此的,主要是参加作家笔会、编辑组稿、记者采访、文化与经济研讨等自由度都比较大的文化活动中,所为、所见、所闻、所思、所游、所交往,按出行时间顺序排列。巧的是,我们国家这三十多年变动之巨,幅度之大、震荡之烈、对社会影响之深,完全值得载入史册,一些景物,今天我们所见,和我所记的完全两种气象了,像新疆的高昌古城,我见到的,是羊群在残垣断壁间随意拉屎撒尿的地方;又像潮州韩江上的广济桥,是中国四大古桥之一,我所见的,只是在废旧的桥墩上用水泥堆砌出原有的形式,帮人想象国内唯一的集梁桥、浮桥、拱桥于一体的建筑是什么样子,今天不仅恢复了原貌,也竭尽了当代的奢华。这些巨变,通过堪称社会精英的这些作家、教授、专家的认识、思考活动,展示于人、存录于世,其价值更是无可替代;同样,也因这三十多年巨变中同质化所造成的弊端,给我们提供思考的空间。至于终止于2009年,不是我在这一条“生命”之“路”上没有继续“走”,而是1992年开始我用电脑写作,使用的是五笔字型,虽不存在“握笔忘字”的烦恼,但毕竟是在机械上敲键盘的事,日久天长,逐渐形成以握笔为累,以携带笔记本电脑为麻烦,让“旧病”复发,日记虽记,笔杆虽用,却只用以备忘,不想详细记录了。当然,最重要的,我所定义的“生命在路上”,意味着山明水秀,桃红柳绿,鸟兽共生,四季变化,东西各异,南北不同,这种异质变换所激发出来的活力,经过这些年以除旧更新之名的同质化巨变,消磨了我急于记录的激情。
关于景点,我所到的,对于多数朋友都不陌生。但一百个人眼中就有一百个哈姆雷特,自然景观、人文景观,同样如此。我写的,只能是我眼中的那个时间点的景物。比如扬州的瘦西湖,借西湖以展其美,可以理解,但何以用“瘦”状之?我以我“眼”纠正了历代引用汪沆之诗而得名的错误,找回“瘦”的真正原因。但是,我相信,读者从我眼中这一个“哈姆雷特”身上,更多的是感受到岁月的温度。岁月温度,总是体现在人的身上,体现在种种细节之中。我关注的,始终是“风物”而非景物。置于前者的“风”,是民风,是世态,“物”才是景物,而且都是当时的,为此特别注意细节上的特点,包括林木、庄稼、建筑,耕作方式,甚至河水的颜色。到边远如新疆、黑龙江等少数民族聚居处,必争取进入家庭内看看其摆设与风俗。更注意比较沿途之风尚。在四川乐山,我受到大佛脚下不知名朋友的一再热情帮助。又如国际都市香港,面对其城市格局,忍不住要去追寻中国传统文化的痕迹,隔着维多利亚港湾的那些观感,我相信那属于我独有。
“庐山烟雨浙江潮,未至千般恨不消;到得还来别无事,庐山烟雨浙江潮。”这是苏轼临终前总结自己人生体验的诗作,参透了禅悟,注满了哲理。我不及其万一,但回望我这一条生命之路,时代、社会提供给我足够的条件,让我游历了不少地方,直至看山仍是山,看水仍是水,最大的价值,也就是沿途的风景。今天,白首忘机,不嫌粗鄙,整理成书,希望告诉读者的,与这位居士大诗人的人生感悟相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