长久以来,地处浙南的温州因山重水复、交通不便,而成为“遥远”的代名词。唐代时,孟浩然从长安出发前往永嘉,先是水陆并进,继而扬帆出海,漫漫旅途中,不禁发出了“借问同舟客,何时到永嘉”的感慨。1946年,张爱玲从上海到温州寻夫,一走就是个把月。改革开放后,“汽车跳,温州到”一度成为温州交通的真实写照,彼时从杭州乘汽车到温州,动辄耗时一整天……
谁能想到,昔日“行路难”的温州,如今到杭州只需一小时?7月30日,新建杭州至温州高速铁路进入试运行阶段,全线进入开通运营倒计时,杭州、温州实现一小时通达。杭温高铁北起杭州市桐庐东站,途经金华市浦江县、义乌市、东阳市、磐安县,台州市仙居县,至温州市温州北站后,利用既有杭深铁路延伸至温州南站,全线设桐庐东、浦江、义乌、横店、磐安、仙居、楠溪江、温州北、温州南九座车站。
杭温高铁,不仅快,而且美。时已立秋,浙南仍是一派绿意。它游走于林木丰茂的丘陵,穿行于小桥流水的市镇,一路青山秀水,一路橙红橘绿,一路人烟辐辏,一路岚霭滴衣。正所谓:近南风景不曾秋,一路山水一路歌。(刘小方)
楠溪江,在雁荡诸峰和括苍山脉的包围中千回百转。在浙江省永嘉县腹地,溪流渐趋平缓,冲积成曲折宽阔的江湾,形成一片河谷平原。那些依水而筑的古村落,就散布在附近。
五代后周时期,福建长溪人李岑为了躲避战乱,拖家挈口,跋山涉水,至楠溪江上游一带,但见“山峰挺秀,涧水呈奇,人生其地者,皆慧中而秀外,温文而尔雅”。于是,他们停下迁徙的脚步,辟地结庐,繁衍生息,并以苍墩为村名。后因避讳,改名苍坡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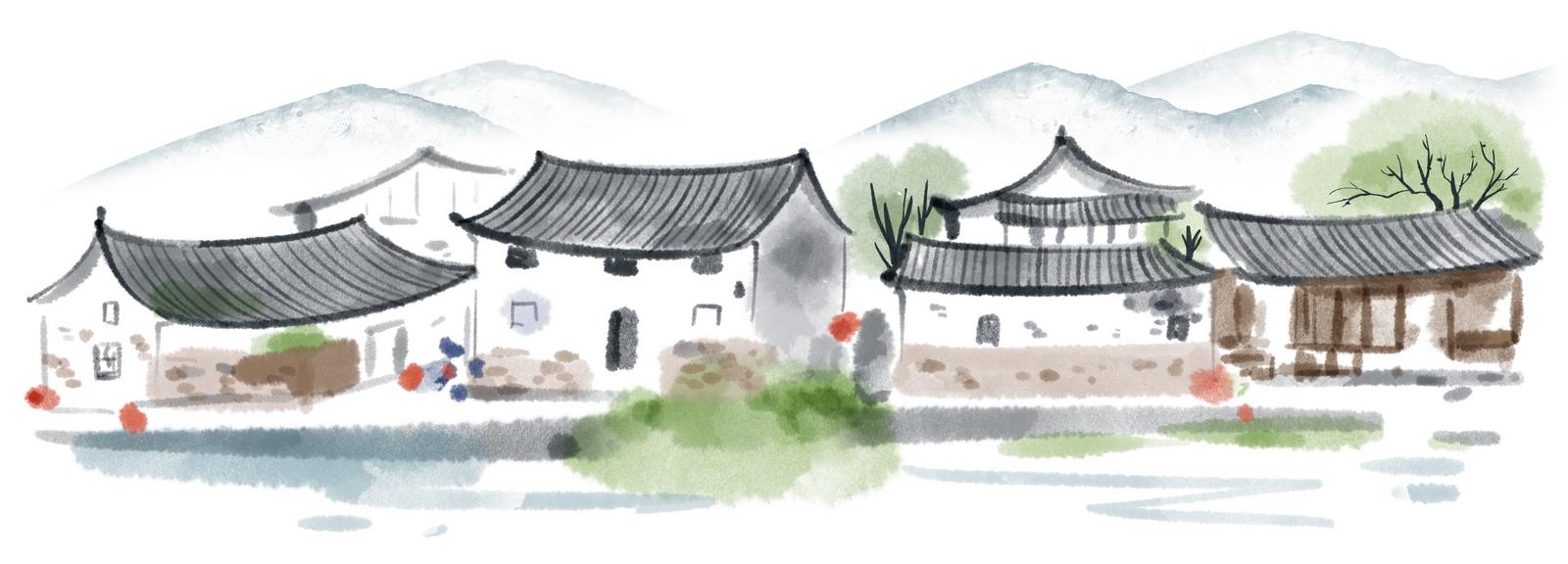
苍坡的先民,是见了世面的,从村庄的建筑上可窥一斑。农耕时代,对自然的亲近和崇拜,是建筑学上朴素的审美观念,落实在规划布局上,往往讲究“山环水抱必有气”的风水格局。借自然山水,融文房四宝,诠释耕读传家的理想。如今,走进苍坡的每一个人,仍为其缜密有序、精致贯通的布局叫绝。
苍坡是一个封闭式的村寨,背依笔架山,面临楠溪江。用鹅卵石块垒砌的寨墙院墙围成方形,护佑着村庄。村口有一座木牌楼,以大斗、小斗、托梁、挑檐组成,予人庄重古朴的感觉。上悬方正的匾额,书“苍坡溪门”四个大字。进入村口,须得跨过三级条石砌成的台阶。“三试阶”,鼓励村民通过府试、乡试、会试,以登天子堂。紧密连接“三试阶”的七级台阶,长约20米,铭记李姓子孙因政绩显赫连升七级的荣耀。村民将这七级台阶,命名为“进士坦”。入村必经的小桥,由石条搭建而成,窄窄的,貌不惊人,寓意却深:五块大小匀称的拱形石条,似墨锭。一条长达300多米的鹅卵石主街,悠长如梦,牵引我们的目光迎向一排三座各自突起却相互联结的山峰。当地人称它们为笔街和笔架山。笔街两侧各有宽阔的方形莲池,似砚。西池用来日常洗涤,洗衣妇可以从掌间感受清水的抚摩。东池环绕宗祠、庙宇,传承着家族训导和对先祖的敬祀。村外的几千亩平畴则是一张巨大的宣纸,任由子孙落笔生辉。
一个走过千余年风雨的家族,一定会留下一些亘古不变的东西。在望兄亭,我找到了答案。苍坡村东南角有亭,四面敞开,檐角飞翘,披檐舒缓,与方巷村的送弟阁遥遥相望。关于这对亭阁,还有感人的故事。相传,苍坡李氏七世祖兄弟俩感情深厚,成年后另立门户,弟弟留守老宅,哥哥去方巷村开基立业。两人白天忙于劳作,晚上才有空面聊。一旦坐聊,话语不休,不知不觉夜便深了。哥哥执意送弟弟回家,弟弟免不了返送。如此往复,晨曦已初露。于是,兄弟俩约定:各自在村里造一座亭阁,平安到达自己的村庄后,便在亭阁上挂灯笼以报平安。
故事,讲述村民的内心憧憬。兄友弟恭,这种笃爱和睦源自血缘,源自本性。北宋末年,苍坡李氏八世祖李霞溪的兄长奉命出征,战死在抗辽前线。李霞溪毅然辞官还乡,扛起照顾哥哥一家的重任,在东池中央筑水月堂寄托哀思。水月堂,屋脊灵动,四面有重檐。堂南端辟一小院,内挖小池,如明镜镶嵌,可鉴日月。
孝悌行于家,乃有仁爱施于人。楠溪江上多矴步桥,村民聚石水中,以备涉溪。一步置一石墩为母矴,隔六七步另附一子矴,以便行人避让。那日,我空手过溪,于石矴上遇一挑担村民。老汉于几米之外止步谦让。我心生感激,停步道谢。老汉咧开双唇,缓缓说起李氏族范:行矴步之上,男让女,长让幼。老汉嘴里吐出的每一个字,都是从先祖那儿继承的君子气质。
四通八达的青石路,将我们引向村庄深处。笔街两侧的民居极有特色,矮墙将宅院包围成严谨整齐的独立空间,偏有瓦松、蓬草不甘寂寞地探出石墙,以点滴葱茏,串联起若有若无的沟通。家家户户都有阔大的廊檐,檐下角落堆放一些农具。夏日迟缓的风,吹来妇人寥寥几句家常对话,方言口音浓重,我几乎听不懂。每一个院子,都有农妇在晒红豆、豇豆。竹筛搭在门前,也搁在矮墙上。我凑近去闻,经过阳光曝晒沉淀下来的气味,暖热黏稠。“冬晒萝卜生姜夏晒豆。当季吃不完的,晒干,留待日后慢慢吃。”边上稍年轻的女子用普通话告诉我:“自己家种的,自己晒的,吃味好。”我承认,我有片刻的出神。这种熏染了岁月尘烟和农耕传统的生活方式,是时间非常充裕的旧年月里才有的细节。
在一道旧拱门前,遇到躺在手拉车上瞌睡的老人。他干枯得像一根干豆角。老人微眯着双眼,被我们的脚步惊动之后,略欠了欠身子,右手遮在前额,试探了阳光挂在马头墙上的高度,很快又耷下去,放心地潜回杳杳旧梦里。日子可以很慢很慢,这是他安静地与自然相处的方式,也是凭吊过往的方式。
绕完民居的东北边,算是到了村庄外围。天蓝得令人发晕,云朵像是撒开四蹄的白兔。一鉴方塘,水面并不辽阔,是狭长的区域。风吹涟漪,漾开细碎的下凹的弧面。岸上遍植杂树。最壮硕的榕树,黑褐色的枝干苍凉,偏长出一树繁华,欹依倾斜,将万千枝叶披垂,绿荫连着绿荫,营造出“城中如火热,此地独清凉”的惬意。隔了水岸,便是一马平川的沃野。晚稻插下不久,秧苗随风起伏,形成明朗的线条。孤注一掷的青黛盘桓在水天之间,飘浮起流动的绿意。置身其间,好像观赏一部田园抒情短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