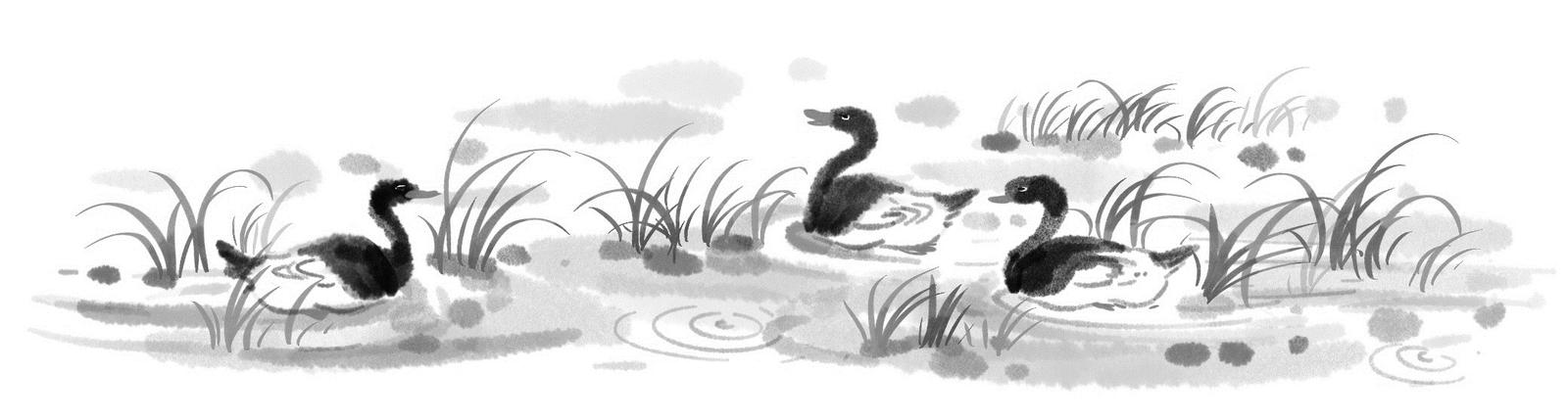□ 胡启涌
贵州从江,翠碧如练的都柳江从北到南蜿蜒而过,散落两岸的苗家吊脚楼在晨雾暮岚中躲躲藏藏,隐隐约约,若不是一只渔舟划波破雾而来,还真以为置身在一幅宋代山水画中。
从江县加榜梯田有近1万亩,其中党扭、加页、从平、平引、摆别、摆党是梯田的“重彩”之地。我一阵迟疑之后,选择从党扭一组走进“青蛙一跳三块田”的梯田世界,走进大山里的鱼米之乡。
这里的梯田层层相铺,丘丘错叠,如一册随意翻开的巨型书本,读哪一页都是水灵灵的诗句。那些点缀其间的苗家吊脚楼,多则20多户,少则几家,就是一张张精巧的书签了,时刻等着你的再次阅读。
梯田紧靠都柳江支流加车河,终年雨水充沛,气候温润。每天清晨云雾从河边缓缓升起,给梯田披上一层轻纱,梯田、村舍时现时隐,缥缈迷离。夏季的风说来就来,呼啦啦几下把轻纱掀开,顺山而下的梯田于是一览无余,尽现眼前。大山里的风调皮地逗弄着墨绿喜人的秧苗,秧苗也主动迎上去问候山风,一阵暖心的互动让大山夏意荡漾。几位苗家妇女没时间搭理无遮无拦的山风,腰系竹篓,绾起裤腿,俯身在秧田里,不时将捉到的鱼儿放进竹篓,惊起几只觅食的秧鸡和白鹭,舒翅飞向另一丘稻田。
苗寨被梯田包围着,被夏天的绿色包围着,宁静、恬淡。走进苗寨,一幢幢由杉木构建的吊脚楼随意坐落在层层绿浪之上,无依无附,单独成幢,像一个个麦堆似的。苗家人将蜡染后的土布晾晒在楼栏上,山风吹来,宽大的布匹随风摆动,“噗噗噗”的声音给苗寨增添了几许生动。行走寨中,正逢一位盛装的苗家姑娘款款走来,继而消失在一条石板小路的拐角处。环顾四望,不见倩影,迷茫间,一阵动听的歌声不知从何处飘来。我顺着一条曲曲的小路循声觅去,只见一座芭蕉半掩的吊脚楼上,一位苗家姑娘坐在阳台的美人靠上绣花走线,忘情歌唱。我没有打扰她,悄悄绕过木楼,往寨子深处走去,而这一人、一楼、一首苗歌,令我一再回望。寨子中有一块平整的坝子,应是大家聚集的地方,墙根下摆放着一些不规则的石块,几位老媪闲坐其上,忙着手上的针线活。几位老翁也扎在一起,唠着什么。
据志书记载,从江苗族的祖先曾居住在东南沿海,因为战乱辗转迁徙至此定居。虽然远离江南水乡,但他们仍然保留着“饭稻羹鱼”的传统生活习惯,至今已有1400多年了。苗家建筑物的板壁上、门楣上,随处雕刻有大小各异的鱼形纹,就连小路、过道、踩歌堂都是用鹅卵石精心铺设的鱼鳞纹和鱼骨纹。鱼在苗家人的心中是故乡,是乡愁。水田里、山塘里都喂养有鱼,住房上、服饰上也有浓郁的鱼文化。民俗专家说,苗族人的这种习俗,是为了怀想曾生活在水乡的祖先而养成的。
苗族同胞来到远离水乡的加榜后,虽然散居在大山里,但世代都自觉遵循“种植一季稻、放养一批鱼、饲养一群鸭”的传统农业生产方式。每年谷雨前后,加榜苗家就将秧苗插进水田,然后把鱼苗投放到稻田里。等到鱼苗长到三寸长左右,再把鸭苗放入稻田。这时的鸭苗无法捕食田鱼,两者同生稻田,彼此无害。鱼和鸭在各自的觅食过程中,不断啄食稻田里的水生植物和昆虫,同时翻松田泥,增加水中的氧气含量,其排泄物又提供了秧苗成长所需的有机肥。这种稻鱼鸭三赢的传统方式,不用农药和化肥,实现了生态环境的平衡。
加榜的稻鱼鸭不同寻常,都是这方山水赐予的。苗家人喜欢食用糯米,香禾糯是从江县特有的地方优质水稻品种,米粒饱满,色泽洁白,酥香软糯,黏而不腻。田鱼是苗家人多年驯化而成的小个头鲤鱼,颜色有橙红、花斑、白色、黑色等,是苗家赖以为生的主要食材之一。苗家人驯化的特有鸭种小香鸭体形较小,区别于常见的家鸭。它们灵活穿梭在秧行之间,恰到好处地翻松田泥,除虫增氧。
加榜梯田是藏在大山里的鱼米之乡。梯田如书册,一日难阅尽。我决定在一户苗家住上一宿,看看月光中的梯田,听听夏夜的蛙鸣蛩叫,再与苗家人畅饮几碗香禾糯酿制的“煨酒”,于“稻花香里说丰年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