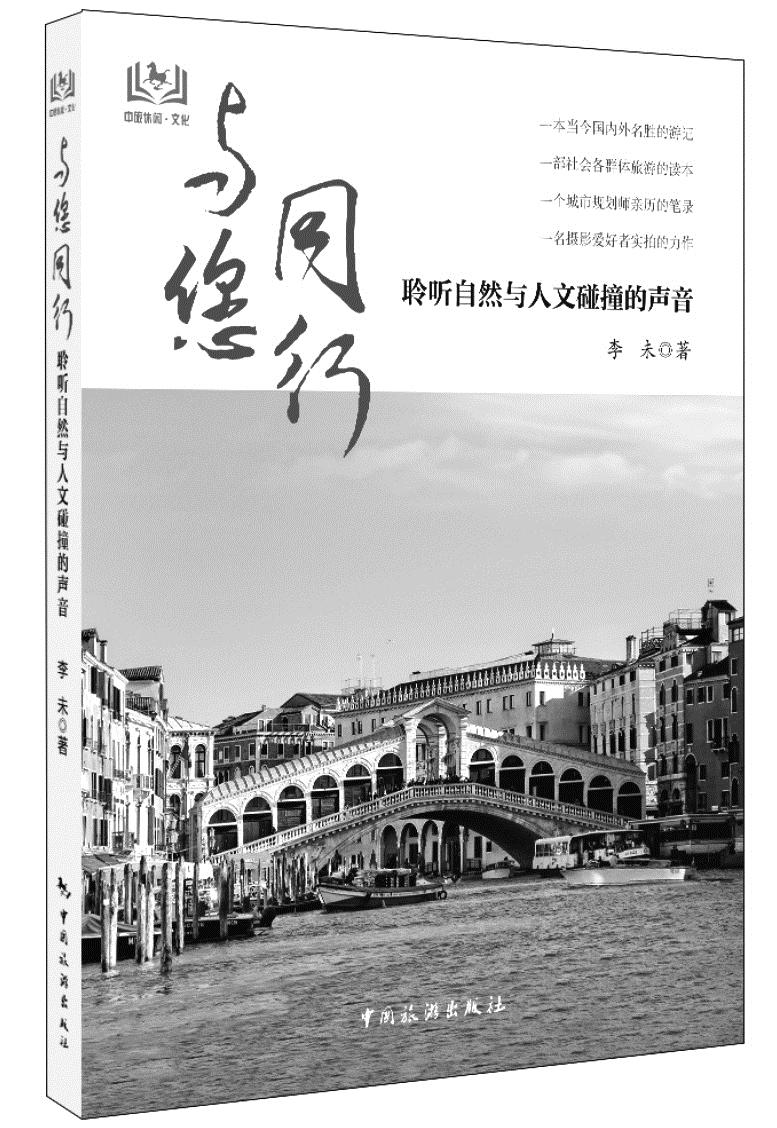论起改革开放以来全民都有共感的成果,我想,热度至今不减的旅游大潮肯定算一个。“世界这么大,我想去看看”,一句话道出了国人的心声。旅游热不仅开阔了人的眼界,撬动了经济杠杆,还带起了游记写作与摄影的兴盛。过去几千年,游而记之只能算是文人舞文弄墨的专利,你再看,现在各种媒体上的纪游文字,谁能说得清写手什么来路?有各式各样的旅游,就有各式各样的写家,自然生出各式各样的游记。老实说,看多了,记不住。
近日读到湖北李未的游记集《与您同行》,心中为之一动,这倒不尽是与作者有过一面之缘。原以为在书中找一些自己没去过的地方,看看新鲜,长见识,以享卧游之便,没想触碰到了作者执笔时的一片诚挚的文心,不免读得细些,引发了联想。如今的游记,多是停留在耳目之间的印象,有些甚至把感受的官能让渡给了照相机,人到场了,心不在场,一堆照片成了旅行归来唯一的收获,临到动笔,只能以照片为依凭。李未不同,他的游记不仅有观感、有形象,而且文字中处处活跃着一颗好学习、善思考的心,心思藏在文字中,读者阅读时有所会意,无形中调动起了自己的经验,各自的感受隔着景物相互擦出火花,形成思想的涟漪,“心有灵犀一点通”,这就是文学的魅力吧。
我也是个爱跑的人,常常爱一个人跑。有时借着组稿或开会出去,人多,不尽意,活动结束一个人再跑。庐山上过两次,印象中全是与同行者在聊天,没有留下一行文字。读到李未《庐山:至今不识真面目》,劈头一句:“其实,我不想再上庐山。”一下就把我吸引住了。紧接着:“但是,这却是我第三次上庐山了。”开篇好有张力,雾中庐山一样,似乎隐藏着无穷的起伏。作者并非卖关子,故弄玄虚。他3次上庐山,前后38年,恰好在人生经历的不同阶段,他把自己与庐山放在大时代中,集中表现3次以不同身份看庐山,关注点的迭变,以个人的眼光,折射出时世变迁,今非昔比。庐山褪去了政治色彩,回归自然本色、人文地位,很多过去到过的地方,有了新的发现,也有的地方过度商业化,多了些金钱的俗味。作者抚今追昔,发出这样的感叹:“三上庐山,三种身份,三种心情。回眸历史,展望未来。历史就是历史,时间能够诠释一切,唯其如此,有些自然景观与人文现象,几近相似,看得见,摸不着,为什么?”作者没有给出答案,直接以文题“庐山,至今不识真面目”做了文尾,给读者留下思索的空间。与其说这是一篇游记,不如说是李未借由庐山,反思历史,回顾人生发出的感悟。
有些旅游者,往往将旅途与日常生活刻意区分开,追求另类的纯净。李未相反,他的旅行紧紧贴着他的日常生活,将旅途中感受到的“自然与人文碰撞的声音”,与故乡、亲情、家庭、工作融合在一起,应该说,李未是把旅行当作生活的一部分,并非一种例外或是补充,他的游记也就真实地照出了他的生活状态和品性,形成了自己的特色。
作为一个城市规划师、建筑设计师,巴黎是不可不去,不可不写的。“好些年了,我一直想有机会去趟巴黎,这不仅是年轻人对‘时尚之都’的向往,更是规划师对历史古都的神往。”行前,李未做足了功课,“为了了解巴黎,我倾听先行者的述说,查看亲历者的留影,收集揽胜者的文字”;旅途中,“我既当游人,又当文人,既忙摄像,又兼速记”;回来后,“为了品味巴黎,我反复浏览珍贵的瞬间影像,认真搜寻切身的零碎记忆,仔细回味曾经的感受感想。”正是这样以认真敬业的职业操守贯注于旅行,使他巴黎之行游记得以提炼出红、黄、绿、蓝、紫5种颜色的城市观感,专业而不乏文学性,令人耳目一新。
李未出生、工作在湖北荆州,祖籍是四川自贡,自称“蜀人楚子”,大家庭的表亲们都定居成都,他认成都为“表故乡”,几乎每年都要回成都寻找一下故乡的感觉,品味一番家乡的味道。李未的文字还真有几分四川人的幽默。他写成都的游记,瞩目于宽窄巷子:“只要一有机会到成都,我都会去宽窄巷子感受成都人那种悠闲的调调,春夏秋冬不同季节,游过、待过、品过、闲过、泡过,那感受颇为温馨。”;“我在宽窄巷子里的视角总与规划建设有关,关注点不是规划布局,就是建筑形式。”他眼中的宽窄巷子俨然是老城区改造的典范,“商家店铺与院落墙壁间隔,文化景点与私家住宅穿插,游览的节奏跌宕起伏,富有韵律,游客既不会审美疲劳,又不致山穷水尽。”与在巴黎的客观考量不同,写成都游记,专业视角中融着浓浓的乡情。他期盼自己的故乡荆州,也能塑造出具有“三国名城,楚都故里”韵味的历史文化街区。
还别说,李未认为自己是荆州与生俱来的“游客”,责无旁贷地写了一篇《穿越时空‘游’荆州》,“我眼中的荆州,有童年的记忆,有少年的感觉,有青年的印象,有中年的感悟……有审视历史的痕迹,有观察现代的心理,有眺望未来的梦想。总之,是穿越了时空隧道的,不仅是身游,还是‘心游’,更是‘神游’。”他把自己的人生经历,当作历史的荆州与今日的荆州交汇点上的见证,为家乡打造了一张文化名片。
李未重感情,刚与哈尔滨结下了儿女亲家的缘分,就有隆冬季节牡丹江雪乡之行。他的雪乡游记,用心渲染一个“暖”字,“沿着雪韵大街一直溜达到尽头,洁白的雪铺满整个村庄,各家各户挂满了金黄色的玉米和大红色的灯笼,各种各样与雪有关的杂货,陈列在以雪垒成的货架上,摆满了街头。洁白如玉的白雪,在大红灯笼的照耀下,宛若天上的朵朵白云飘落人间,幻化无穷,无限喜庆的气氛令人有种节日团圆的美感。”雪乡的暖衬起作者心中的暖,满满的都是对未来的憧憬。
游记中最动人的亲情抒写,还是《相逢在纽约》。儿子大学毕业后被派驻纽约,李未参加赴美访问团,与儿子在纽约有半天的相聚,文章先是简述儿子的成长,以“多年父子如兄弟”而自豪,从访问团一踏上美国西海岸,儿子几乎全程微信跟踪,洛杉矶、华盛顿、费城,沿途一个个城市的宏观优劣、景观特色,在父子两代人交流中呈现出来。“奇怪的是,我们父子在不同时间,从不同的视角,以不同的阅历而所见所闻竟感知相近,感觉相同,感受如此相似。”在纽约当面交流,没想到,仅仅两天的见闻和思考,竟博得常住纽约的儿子的同感。分手的一刻最难忘,“我们默默地走进地铁,走向长途汽车站,这好一段路程,我甚至忘记了职业的习惯,忘记看一看纽约的地铁与公共交通究竟是什么样。恍惚中只记得他送我回到了酒店,又要乘车返程。儿子拎着我带给他的东西,回头望望,迟疑片刻,登上了汽车,等我缓过神来,车已驶出车站,隐隐看见儿子在挥手致意,我则再也控制不住,眼泪夺眶而出……”
李未的游记写作,不只在情与景上下功夫,往往是调动起自己全部生活积累,反复联想、比较、提炼,思有所得,方才命笔。他的游记并不拘于一格,甚至带有传记的某些成分。
中国古代大约没有“旅游”这个字眼,旅行中的一个“行”字,大多寓有文人“读万卷书,行万里路”的情怀,探求的意味浓,游憩的气息淡。当代人写游记,当然不必蹈袭前人的窠臼,然有志于游记写作的朋友,还是要取法乎上,从经典中汲取营养,有心,用心,才能写出让读者动心的文字。
顺带说一句,书中配有不少作者自拍的摄影作品,文图并茂。感觉中,照片过于严整,大多像是景区身份证上的照片,缺少惊鸿一瞥的发现。如果能以写散文的心态,拍一些有个性的瞬间,是否与文字搭配起来,更协调呢?
2021年2月2日于津门
(谢大光,著名作家,曾任百花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、《散文》编辑、《小说家》主编、《中外散文选萃》主编,其作品《落花枝头》《鼎湖山听泉》等被收入中学语文课本。)